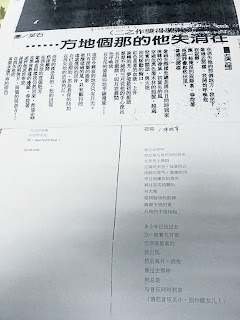诗的尸毒散发成烟
我终要有自己的演化
耽溺是不对的
如此卑屈的眼神也是错
确定,
永远坚信
———陈强华〈支撑睡意写诗〉(《幸福地下道》)
这是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案例,也可能是马华文学上最夸张的抄袭案。
陈强华大我7岁(1960年生),长期在华文独中教书,组诗社、鼓励年轻人,对诗有激情,是很多文艺青年的启蒙老师。“作育英才无数”,并非虚言。如果当年他毕业后是到我的母校教书,也可能会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事发后,学生朋友的文章都写得相当动人,多半清楚表态对抄袭的不认同,但也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出道三十多年的名诗人会去大规模的抄袭(鸿鸿指出至少有8年,自2005以来)?为什么这么明目张胆的、大量、直接的抄,仿佛呈现为“过度证据”?斥骂、丢石头当然很容易,但如何提出一种解释?这整件事不合逻辑啊。是他的创作观出问题吗?为什么那么多年没人发现———从发表到出版,他的读者、学生,都一无所悉?简直匪夷所思。这也让整个马华文学界不得不分摊这事件的风险。
关心马华文学的人几乎都百思不解,也都试图了解是不是还有可以为他辩解的———譬如他的离婚、他的忧郁症、药物的副作用、他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在“以诗养病”的过程中产生幻觉等。如他学生所说,抄录作为疗病之用的诗误渗进去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后又有阴谋论之说,门徒出卖导师之说,俨然是一出小型的悲剧(或典型的烂片)。假使门徒早就发现了导师的秘密,他们可能劝得动吗?
即使8年来的“烂泥系列”可以以病辩解,对我们来说,最担心的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一旦发现早期作品也是如此(那都是公开发表的作品,迟早被查出来的),那反而立即可以宣布,鸿鸿与(香港)陈某的贴文其实即已宣告诗人陈强华诗人生涯的结束,剩下的就只是葬礼与悼词了。
这基本事实面如果确立,就不必再辩解,也不必转移焦点,阴谋论云云都不重要了。“叛徒”反而可能是“大义灭师”呢。
昨日(8月3日)媒体界的朋友出示一份剪报资料,陈强华2006年出版的诗集《挖掘保留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有一首诗〈莅临〉(发表于1993~1998间,p73)与第15届联合报文学奖新诗第二名的〈在消失他的那个地方〉(作者吴莹,发表于1993,收入痖弦主编《小说潮:联合报第15届小说奖暨附设报道文学奖、新诗奖作品集》联经,1993)高度雷同,当年他曾向作者示警,但强华显然不以为意。而其时运用的“手法”,和最近被举发的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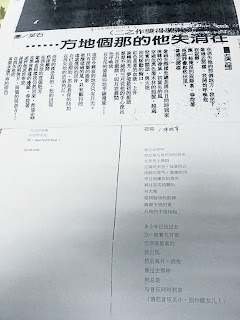 |
| 吴莹与陈强华的诗对照(黄锦树提供) |
〈在消失他的那个地方〉第二段
像过去那样他总是与白日同时到来
流转的香气, 初诞生的风
穿过他黑色灌木林的短发, 越过
坚实的额头, 与大地
相同脉动的胸口
红色星星的血液,
上升
旋转的光, 梦境最初的源头
源源不绝的三月从他手心流出
五月在眼睛,
四月在唇间
他呼唤我
百合花的清晨向地平线漫延……
〈莅临〉陈强华
像过去那样
她总是与音乐同时到来
在梦田上舞蹈
辽阔的天空,
低垂的云
流转的香气,
微微的风
穿过她瀑布的黑发
越过坚实的额头
与大地
相同脉动的韵律
源源不绝的爱
从她的手指扬起
拼贴重组,换几个字,但原诗其实更有诗意更有韵味。
我一直猜想是不是跟他眼高手低、及他理解的“后现代主义”有关。
1980年左右留台的陈强华,恰逢台湾现代诗的转型期。
1984年夏宇(黄庆绮,1956)自费出版了划时代的诗集《备忘录》;被60后世代称为“教皇”的罗智成(1955)在70、80年代发表了大量极有影响力的诗作,屡得大奖。从《画册》(1975)、《光之书》(1979)到《宝宝之书》(1988),彼时的文青无不深受影响。再如杨泽(1954)有广泛影响力的《蔷薇学派的诞生》(1977)、《仿佛在君父的城邦》(1980),也在那些年出版了。这些广泛被模仿与借镜的诗在强华早期的诗作中有多少投影,也待有心人清查。虽然这些作品未必尽被归于后现代主义。
台湾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根据一般的说法,始于1980年代上半叶,诗方面是夏宇、罗青、林燿德,留美返台的学者蔡源湟、台湾本土博士张汉良等的极力鼓吹,孟樊在《台湾大百科‧后现代主义》辞条上归纳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性,诸如反体裁、反身性、互文性、语言游戏、拼贴、碎片化(这些都已是陈腔滥调了)与及个中核心观念之一的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的“作者已死”论。
身为小几岁的同代人,事发后我最直觉的反应是,会不会是他的创作观出了问题?他是不是受到某种后现代理论的误导?罗兰‧巴特“文本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其他文本存在于它的不同层面,呈现为或多或少可辨识的形式: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语的重新编织。”(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以为写作就是剪裁拼贴,写作者即抄写者,它编织文本,而作者已死,后现代抄写者具有无上权力(〈作者之死〉)。从这角度来看,这事件基本上还是个文学事件。也许他会自以为是一种马华后现代的文学行动也说不定。
台湾学界对理论的接受一向生吞活剥、不求甚解、各取所需;这样无政府主义的文本论、作者已死论、无限互文论(加上影响焦虑论)似乎可以为(欠缺才能、自信与道德自律)的有心人大开方便之门,或至少好似可以正当化某种剽窃行为。但如果那是文学行动,是为了挑战马华文学的体制,唾弃既有的文学观,就不该发表———或不该领取稿费;更不该收录并出版成诗集并把自己的名字印上去作为作者,更别说去参加文学奖并领取奖金奖座———这些都是体制化的行为。
其实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论老早就受到他的同代人傅柯的修正。作者在西方是现代的产物,它和法律上的言论刑责有直接的关连,也衔接着私有财产权(傅柯,〈什么是作者?〉)。因此一旦“收录并出版成诗集把自己的名字印上去作为作者”,作为文学行动就破产了,而且只怕还有法律上的责任(侵犯他人的智慧财产权)。
马华文学的写作者长期、单向的向大中国文化区(及世界文学)吸收养份,也必然长期的承受着压力。再怎么努力也处于边缘,让有些人急于加入它。但也可能发展出一种书写策略,譬如我自己多年以前谈的“再生产的恐怖主义”(《梦与猪与黎明》序),在写作上和大中国文化区、甚至世界文学尽可能的纠缠(互文上的纠缠),“一切可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除了抄袭。
因为我们必须是作者,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限制的作者,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消化得掉的才能吞啊。抄袭作为另一种可能发生的反应(一种厚颜无耻的致意),当然也是种吞噬的行为。把自己达不到的都吞下来,但因为胃不够强,没办法消化(吐出来后当事人还认得出那些尸骸的脸),甚至常常点金成铁。
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在讨论傅柯的鲁塞尔(一个疯掉的作家)研究时,提出一个说法,“更应该说是鲁塞尔在语言中生了病,这种病也是语言本身的疾病,是文学以典范的方式展示其特征的疾病。”(〈鲁塞尔的读者傅柯:作为哲学的文学〉《文学在思考什么?》)那是一种怎样的病呢?“语言其实陈述着虚空、缺席”。作者引马拉美,评述说:“诗歌就是语言的这种极限形式,在诗歌中,语言不再说任何东西:诗歌将人们引向现实与事物的边界,在那里事物变成了,或重新变成了‘虚无’,因为它们除了被说出来之外就什么都不是,而且关于它们所说的东西,就是它们‘存在’这个虚无。”(p290)疯掉的鲁塞尔凝视那死亡的虚无,也许正因为凝视那死亡而致疯。模仿马舍雷的讲法,陈强华这种难以解释的行为只可以说是“他在诗里生了病”,那源于对诗的爱,“爱到痴时即是魔”(陈仪),以致越界了,坠入无边的虚无。也许他一开始就是个非常挫折的诗人,同代名家像诸神那般遥不可及,而他悲伤的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人的言语不设防的进驻,文心被腐蚀、蛀空。主体从摇摇欲坠至沦丧,心灵被吞噬了。反讽的应证了“我即他人”(Je
est un autre),“我会是那彻底删去了的那段过去”(陈强华,〈过去式〉)。
面对那样的诗观和写作方式,除了告别、哀悼,我们还能做什么?
*(本文以我这个礼拜以来在脸书上不同地方的留言为基础,也用了若干朋友私讯中的材料甚至言辞,恕不一一注出了。)
8月4日埔里